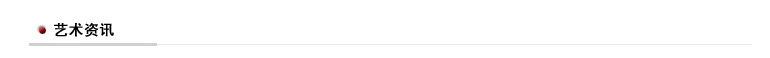|
作为一个摄影师,我最近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整理过去拍摄的底片和影像。近些年来,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运转,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乡村面貌更是日新月异,过去的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的记忆。当手指轻轻划过胶片,就像触摸那些沉睡灵魂,岁月已让它伤痕累累,记忆的片段也随之浮现。此时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关于贵州六枝长角苗的影像记录,是我着手于二十年前的“贵州六枝长角苗妇女影像调查”中的片段。


照片带我回到1995年,我第一次去梭嘎时看到的场景。长角苗小姑娘熊绍珍正和她的伙伴在村头放羊,阳光洒在她们身上。她轻轻挥动着手上的小藤条,眼里充满了忧伤,常常发呆地望着远方。瘦弱的身体,红彤彤的脸,那时她11岁,只读了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回家。后来我才知道她很想读书。只因家里还有哥哥和弟弟,只能让她放弃,让哥哥弟弟去读,而她小小年纪,就要承担家里的许多活路。

在坡上和小姐妹绣花是她最快乐的时光,小小的绣片寄托了她无数的梦想。这里的女孩从小都要学绣花,一针一线伴随着她们童年的梦和蹉跎的岁月。代代相传,这是苗族文化的重要部分,是穿在身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女性在梭嘎这支苗族所起的作用和地位有别于其他民族。除了生儿育女,还要承担几乎所有的劳动,刺绣、蜡染更是样样精通。他们是山寨真正的主人,她们用坚韧托起大山,用汗水浇灌土地,用柔情书写女性的爱恨情仇,可歌可泣。

整个山寨被荒蛮的大山所困,这里是贵州石漠化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和土豆,产量很少。上山种地也是妇女的事情,她们在岩石上爬高下低,如山羊般轻巧。远远望去,她们的身影仿佛被镶嵌在坚硬的岩石上,融为一体。记得那年政府搞扶贫,让村民上山种金银花。一帮妇女集聚在一起,就是不上山,扶贫干部问其原因,才知道她们是要喝几口酒才去干活。干部只得自掏腰包,打来散酒。这群女汉子大口喝下,便笑着唱着到山坡上干活去了。

这里的主食是玉米,妇女们用它做成各种食物,但由于能耕种的土地很少,产量相对来说就很低了。当地有一顶草帽一窝包谷的说法,也就是说山上哪怕只有一顶草帽大小的土地,就要种下一窝包谷。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梭嘎的妇女们用她们的坚韧和毅力让生命繁衍,让生活继续。

当时对梭嘎苗族夫妇来说,拍张合影是件非常正式的事情。站在自家门口,他们略显紧张,因为从未这样并排站着面对镜头,而影像让他们获得了平等。听说现在到梭嘎拍照是要钱的,妇女们穿戴整齐,被摄影者带到村寨的各个角落“创作”,来去匆匆,之后摄影家们把美好的画面带走。而现在的妇女们仿佛也知道了拍摄者的心思,早早地摆出需要的姿势,让你拍个够。这样的影像侵入,终归有一天会彻底摧毁她们的心灵和文化,从而变成摄影者的理想影像,这种“伪”是摄影者强加于此的。

那时的梭嘎全村只有山下的一口井,所有的生活用水都取自于这里。妇女们用木桶装水压在腰间,倾斜着身体往山上背,一桶水大约有五六十斤,走在山路上,显得十分吃力。可许多搞摄影的就为了拍这样的照片来到梭嘎,认为那就是这个民族的生活特点。作为记录,我拍过关于那口井和背水的生活方式,但我认为,那只是他们艰难生活的写照,并非艺术表现的一道风景。更有甚者,出钱让妇女们排成一队,拍摄他们背水时的宏大场面,让人痛心。在梭嘎的日子里,我常常仰望天空,繁星闪烁,静静的山寨在星光之下愈发美丽。

在梭嘎拍摄时,我常常让她们直视相机,希望影像能穿过镜头,呈现在心灵的镜子上。她们大多数目光炯然,泰然自若,眼中闪烁着人性的光芒。我想这是她们勇于直面艰难、直面生活的态度,是她们千百年来的精神所在。她们对美充满了幻想,当黑色的假发缠绕在头顶的长角上时,她们显得如此的自信和美丽。

梭嘎的三眼萧,可以吹出深沉而委婉的韵音,是我听过的最忧伤的曲调,让我仿佛看到苗族迁徙时那悲壮的场面。他们来自远方,在此安家,时光封存了他们的记忆。而影像却把记忆带走,变成了记录者和观者的记忆。若干年过去了,我常梦回梭嘎。

在梭嘎拍摄“妇女影像调查”的日子里,让我印象深刻的情景随处可见。拍摄时,我对自己说得最多的话,就是拍你看见的,拍你被打动的,拍你不得不拍的。当这对母子俩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大脑神经变得麻木,直到按下快门,眼睛离开取景框的那一瞬间,仿佛才回到现实。这是过后让我凝视最多的一双眼睛,每次相遇我双眼都会充满泪水。

听说寨子里有位年轻的母亲,长得很漂亮,她是从外寨嫁到梭嘎来的。那年的某个冬日,我前去拍她。推门进去时外面的光线也随之照亮了整个屋子和她那美丽脸庞,她本能的抱紧怀中的宝贝。几年后,她带着孩子离开了梭嘎,不知去向。

土豆地里的两个老人是寨子里最年长的妇女。古老的发饰仿佛将山寨所有的秘密深藏于此。他们没有害怕灵魂会被镜头夺走,反而凑近,好奇地看着眼前的相机。在梭嘎长角苗的传统中,长角上缠绕着的应该是祖先的头发,直到离世。年轻的一代开始用黑色的毛线代替,既美观又卫生,但却没有了祖先灵魂的相伴。

土坯墙、茅草房、晾晒在阳光下的蜡染布是梭嘎典型的生活图景。贵州苗族大都生活在高山上,梭嘎苗族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下来本来就是奇迹,这支现存千余人的苗族支系从哪迁徙过来,为何选择此地安身更已无法考证。但从她们神秘的图案中我看到了排列和对称,看到了抽象和变形,也看到了秀美和精致,也许其中就藏着有关他们的来龙去脉的密码。


在梭嘎,床是家中唯一的家具,所有值钱的衣物都放在床上。房间的窗户开得很小,因为它根本就不是窗户,只是一个小洞而已。光线斜射下来,照在老人和小孩的脸上,背景变得很暗。在这小小的房间里,我喜欢拍摄这样的照片,只有两双眼睛的相互凝视,两颗心灵的对照,这是一种彼此的坦诚和信任。在这次记录摄影中,我称之为一种境界。



熊绍珍长大了,即将成为别人的新娘,新郎是山那边另一个村寨的小伙。婚礼的当天晚上,在微弱的灯光下,一千元的彩礼经过三人之手,数了一遍又一遍,交给了女方。但是这个彩礼钱得用于女方哥哥娶亲。清晨,寨子里的妇女们为新娘送行,除了男方家带来的伴郎,送亲的队伍也是清一色的女性。我追逐着送行的人们,在晨雾中穿行。新娘脸上洋溢着幸福,她已不再是我第一次到梭嘎看见的那个站在山坡上放羊的黄毛丫头了。

杨安迪(左四)在梭嘎 |